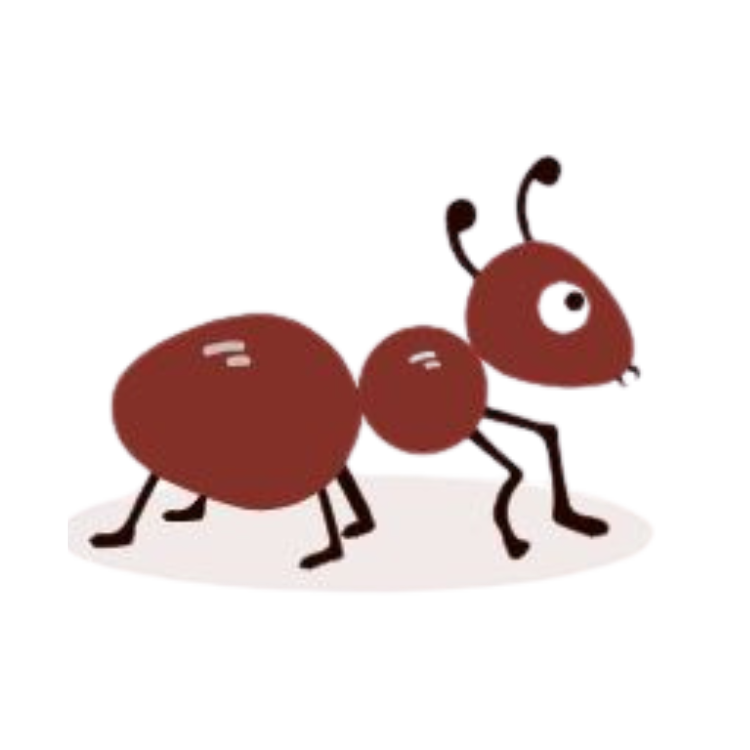远古的足迹:从猿类视角追踪人类表型演化的秘密

人类起源之谜,自古以来就激发着人们无尽的好奇心与想象。无数思想家和科学家投身于这场探索之旅,力求揭开这一千古之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借助化石记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863年,托马斯·赫胥黎在其著作《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首次系统地比较了人类与猿类在解剖结构和行为习性上的异同,提出了“人猿同祖“的理论,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一理论在查尔斯·达尔文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和支持,书中详尽的证据表明,人类同样是演化过程的产物,通过变异、遗传与自然选择,从远古的灵长类祖先逐渐演化而来。
1
为什么研究猿类的物种分化很重要
人类现存最近的亲戚是类人猿(Great apes),它们属于灵长目的高级分类单元,归入人科(Hominidae)和人猿总科(Hominoidea)。类人猿,又称为狭鼻猿类,因为它们的鼻孔朝下,两鼻孔之间有一个狭窄的隔膜。这一类别包含了四个属:黑猩猩属 (Pan, Chimpanzee/Bonobo)、大猩猩属(Gorilla, Gorilla)、猩猩属(Pongo, Orangutan),以及人属(Homo, Human)(图1)。

图1. 已灭绝的古人类和类人猿物种。A.类人猿的演化关系及分歧时间(Pollen et al., 2023);B.古人类复原像。通过人类学技术和化石证据重建早期人类,从右上角逆时针方向: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阿法种、傍人鲍氏种、直立人和弗洛勒斯人;C.普通黑猩猩(Pan troglodytes);D.倭黑猩猩(Pan paniscus);E.西部低地大猩猩(Gorilla gorilla);F.东部山地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G.苏门答腊猩猩(Pongo abelii);H.婆罗洲猩猩(Pongo pygmaeus);I.戴帽长臂猿(Hylobates pileatus);J.黑冠长臂猿(Nomascus siki)。 (图源: B: https://m.khan.co.kr/article/201303152112145#c2b; C & D: ©iStock; E: ©Wikipedia; F: ©Dian Fossey大猩猩基金会; G, H: ©视觉中国; I & J维基百科)。
在这四个属中,黑猩猩和大猩猩是我们最近的亲属。据估计,现代人类的祖先大约在570万至1,000万年前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而与大猩猩祖先的分离则发生在大约720万至1,120万年前;至于与猩猩祖先的分歧,则是在大约1,620万至1,810万年前(Pollen et al., 2023)。
完整的基因组数据为人类、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及猩猩提供了了解这些物种共同祖先分化过程的一扇窗户。通常认为,我们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关系比与大猩猩更为亲近,这一点在早期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了验证(Waterson et al., 2005)。数据显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与人类共享约99%的基因组,而大猩猩与人类共享约98%,红毛猩猩则约为97%。
从猿类的视角来看,人类的表型演化路径充满了复杂而有趣的演变过程。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探究我们与猿类之间共有的演化关系,考察我们相对于其他猿类经历了哪些独特的演化事件,并最终理解那些让人类与众不同的独特适应性特征。
那么,从猿类到今天的人类,我们主要经历了哪些变化呢?早期人类的直立行走、增强的手部操作以及认知能力的提升是人类独特性的重要特征代表(图2)。

图2. 人类演化的几个关键事件:直立行走、工具使用的开始、大脑容量的增加、语言的出现、农业革命、文明的兴起。(图源:https://inf.news/en/science/f43c94ceb780a304f2ae9303033d26a4.html)
2
一步之遥:直立行走带来的革命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史中,直立行走是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它不仅重塑了我们的身体结构,还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文化发展乃至大脑复杂性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解释人类与猿类共同祖先(Last common ancestor, LCA)的脊椎特征对人类直立行走的影响,科学家们提出了两种主要的模型:长背模型(Long-back scenario)和短背模型(Short-back scenario)。
其中,"长背祖先"模型假设,与现代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共同祖先可能拥有五个或更多腰椎骨(Lumbar vertebrae)(图3),数量与长臂猿类似(而黑猩猩只有四个腰椎骨),这可能赋予了脊柱更大的灵活性,从而为人类直立行走和其他运动行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适应性基础。

图3. 长臂猿、黑猩猩和人类的身体平面图。人类通常拥有12个胸椎(Thoracic vertebrae)和5个腰椎(Lumbar vertebra),这一腰椎数量与长臂猿相同。相比之下,黑猩猩则有13个胸椎和4个腰椎,但其椎骨总数与人类相同。黑猩猩的骶骨深度较大,这可能导致其腰椎较为僵硬(Williams et al., 2023)。
控制脊柱灵活度的因素不仅包括腰椎骨的数量,还涉及胸椎到腰椎之间过渡锥骨(Transitional vertebra,TV)的位置、腰椎棘突(Lumbar spinous processes)的方向以及腰椎在髂骨翼之间的夹持状态(Entrapment of lumbar vertebrae between the iliac blades)(图4)。

图4. 腰椎僵硬度的机制。A.人体标本中,T12椎骨作为过渡椎骨,其上关节面朝向背部,而下关节面呈横向,这决定了胸椎的旋转能力以及腰椎的前后移动能力(其中,T11、T12中的T代表胸椎,数字表示从人体背部自上而下计数的胸椎序号;L1则代表紧接着胸椎之后的第一块腰椎);B.在人类中,棘突的方向从胸椎区域中的尾向排列(深灰色)转变为腰椎区域的背向排列(浅灰色),而大猩猩的棘突在整个脊椎区域都保持尾向排列;C.由于高髂嵴和狭窄的骶骨结构,猿类的低位腰椎(白色)可能会受到髂骨的限制(Machnicki and Reno, 2020)。
研究发现,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各自拥有与腰椎僵化相关的独特棘突角度,而人类棘突的形态则与长背的长臂猿以及中新世类人猿更为相似(详细解释见图5)。在“长背祖先”模型中,大猩猩和黑猩猩所具有的较短腰椎可能是在它们各自的演化过程中独立发展出来的特征,而非直接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而来(Machnicki and Reno, 2020)。

图5. 不同物种个体的最后五个胸椎和前三个腰椎的示意图。过渡椎(TV)用红色星号标记。在所有现存的类人猿中,过渡椎通常位于最后一个胸椎的位置。在人类、长臂猿以及猴子中,棘突从过渡椎到腰椎的过程中会发生形态上的改变。黑猩猩的棘突在过渡椎和第一个腰椎(绿色箭头)处展现出类似于长背物种的形态特征,但在第二个腰椎处则恢复为尾向排列。相比之下,红毛猩猩和大猩猩的棘突在整个腰椎列中保持一致的尾向排列(Machnicki and Reno, 2020)。
“短背模型”认为,尽管人类与猿类的最后共同祖先可能拥有短而硬的腰椎,类似于现代类人猿,但人类直立行走的适应性特征可能是独立演化出来的,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到脊椎延长、骨盆重塑及下肢调整等重大变化(图6)(Pilbeam and Young, 2004)。该模型强调,直立行走可能是人类对特定环境条件适应的结果,与其它类人猿的树栖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6. 人类和猿类的骨骼特征比较。两个物种的臀部宽度与高度比,以及臂长与腿长比存在显著的差异(Kun et al., 2024)。
研究表明,直立行走的演化可能是由于森林栖息地的逐渐破碎化,导致早期人类祖先不得不更多地在地面上行走,以便从一个食物资源丰富的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根据现存猿类的行为数据,原始人类最初的两足站立并非是为了在地面上快速移动或作为一种树冠间移动的方式,而是作为一种适应性姿势(Posture),这种站立姿势可能用于在特定环境中提高视野、节约能量或获取其他生存优势,而非作为主要的移动手段(图7)。后期人类两足行走能力的增强,可能与应对复杂变化的环境适应性反应有关(Potts, 1998)。

图7. 早期原始人类演化出两足行走之前的位置行为(Positional behavior)。位置行为是灵长类肢体运动模式研究的一个更为准确的术语(Prost, 1965),它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姿势行为(Postural behavior)和移动行为(Locomotor behavior)(Garber, 1984)。早期原始人类和黑猩猩谱系的最后共同祖先可能展现了多种位置行为,这些行为在现今的灵长类动物中并未完全保留。两足行走并非突然出现在原始人类中,而是在更广泛的中新世猿类的位置行为中逐步演化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足行走逐渐成为了早期原始人类的主要移动方式之一,而黑猩猩则发展出了指关节行走。图中纵坐标的百分比表示在不同物种中,各种位置行为所占的比例,但由于并未展示所有的位置行为,因此总和不等于100%。对于最后共同祖先(LCA)和现代人类的移动行为库组成的推测,仅供参考(Almécija et al., 2021)。
2.1
禄丰古猿对人类运动方式的启示
那么,如何对人类直立行走的起源进行研究呢?
半规管(Semicircular canals)是脊椎动物内耳迷路中负责感知头部旋转运动的器官,由上、后和外三个相互垂直的环状管道组成,内部充满淋巴液(图8)。半规管的形态和尺寸与动物的运动方式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图8. 耳朵的结构及半规管形态展示。A.耳朵结构图;B. 禄丰古猿(PA844)的虚拟左耳迷路结构。红色表示因标本挤压而需要修复的错位部分,浅蓝色表示重建的破损部分。(图源: A: https://ibillxia.github.io/blog/2012/12/21/human-audio-system-out-part/; B: Zhang et al., 2024)
禄丰古猿(Lufengpithecus)是一种生活在约700万到800万年前晚中新世时期的已灭绝古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李强研究团队联合纽约大学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禄丰古猿的内耳骨迷路形态与冠状古猿(如南方古猿露西)以及人类与类人猿的最后共同祖先非常相似,表明它们可能有相似的移动行为。研究推测,古人类的移动行为可能从最初类似于长臂猿式的(Gibbon-like locomotion)站立、树枝下前肢悬挂、树枝上两足行走等方式,逐渐演化为类似于禄丰古猿的移动行为(Lufengpithecus-like locomotion),包括四足行走、树枝下前肢悬挂、垂直攀爬、跳跃、陆地四足奔跑以及短时间的两足直立行走(图9)(Zhang et al., 2024)。

图9. 骨迷路的多形态空间和古人类移动行为演化的概念图。人类的两足行走是从一种类似于禄丰古猿的移动行为演化而来的(Zhang et al., 2024)。
2.2
露西也能直立行走?
大约320万年前,一位名叫“露西”的远古人类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行走。她属于阿法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是我们人类家族树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尽管她的骨骼早已成为化石,但现代科技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她的生活方式。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MRI(磁共振成像)和CT(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扫描了现代人类的肌肉和骨骼结构,创建了数字模型,并根据露西的化石扫描结果,重建了她的肌肉形状和大小(Wiseman, 2023)。结果显示,露西的膝盖伸肌显示出与现代人类相似的特点,这意味着她能够像我们一样直立行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证实了露西不仅能够用双腿行走,而且能够以一种高效、直立的方式进行。
2.3
地猿化石:直立行走的起源
在非洲东部的大裂谷地区发现的地猿化石(Ardipithecus ramidus),属于一种早期的类人猿,被认为是人类和猿类的共同祖先群体的一分子(图10)(White et al., 1994)。化石记录显示,早期的直立行走大约出现在600万年前,这是人类与猿类分道扬镳的重要一步。
尽管对于早期人类祖先所居住的环境(森林斑块与树林草原)仍有争议(Dominguez-Rodrigo, 2014),但对地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研究表明,人类与黑猩猩的最后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森林环境中。早期人类祖先不仅能在树上灵活地以手掌朝下的方式爬行和攀爬,还能在地面上进行比南方古猿更为原始的两足行走,这表明他们的生态栖息地主要是以树林为中心。此外,有观点认为,人类与黑猩猩的最后共同祖先可能比黑猩猩更杂食,它们既在树上也在地面寻找食物,这一假设与地猿的同位素分析结果相吻合(White et al., 2009)。这种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可能为后代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同时也为人类的进一步演化奠定了基础。
图10. 从骨骼到复原的地猿。A. ARA-VP 1/500,地猿的部分骨骼化石;B.完整骨骼的复原图;C.生活状态的复原图(Boisserie, 2010)。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达尔文是如何将两足行走的起源与复杂的适应性联系起来的?达尔文认为两足行走的起源与解放手部进行工具制造和使用有关。随着手部的解放,人类祖先开始使用工具,进而促进了大脑的演化和认知能力的提升。这些进步又反过来推动了更复杂的社交互动和社会结构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文化和文明。
3
智慧的火花:大脑容量增长的背后

究竟是什么使人类这种特殊的生物显得与众不同呢?单从体力角度来看,猿类几乎是“超级英雄”般的存在(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9/03/090330200829.htm)。据研究显示,黑猩猩的力量大约是普通人类的四倍。虽然人类在力量上不如黑猩猩强大,但我们拥有更精细的神经系统来控制肌肉,这使我们能够完成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动作。除此之外,人类还具有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较少的体毛以及更为发达的大脑。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不仅有更为复杂的神经连接,还存在一种被称为纺锤形神经元的独特细胞类型,即冯·艾克诺默神经元(Von Economo neurons, VENs),这些细胞主要集中在与社会情感处理相关的前岛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区域。
当我们谈论社会情感时,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系列人类独有的特性,诸如同情心、内疚感以及羞耻感。一般认为,虽然社会行为在较早期的灵长类动物中已有所体现,但黑猩猩及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在这方面的变化相对于这些祖先类群相对有限。事实上,人类与猿类仍然共享某些原始特质,比如男性间的亲缘关系和强烈的领地意识。不过,人类男性和女性之间通常会建立更为紧密的伴侣关系,从而构建起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架构。而在黑猩猩社会中,雄性和雌性则倾向于依据性别在群体内部形成各自独立的等级制度。
人类与其他猿类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行为变化背后的遗传机制一直是让人着迷的话题。而相关研究揭示,一些细微的遗传变异可能足够引起巨大的社会行为差异。尽管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序列高度相似,但在基因拷贝数变异方面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包括基因的重复、缺失以及倒位等现象。据估计,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组之间的差异约有3%是由结构变异(Structure variations, SVs)造成的,相比之下,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仅占1.2%。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揭示猿类与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遗传差异。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对大猿与猕猴基因组的对比分析,鉴定了大猿特有的结构变异(Great ape-specific structural variants, GSSVs)。研究发现,大约3.4%的GSSVs与神经发育有关,这些遗传变异可能影响了大脑发育的关键过程,例如突触的形成与分化、神经系统的发育以及信号传导机制(Zhou et al., 2023)。
自从人类与其他大猿分化以来,人类大脑经历了显著的体积扩张,但这一过程背后的详细机制仍然是科学界的一个谜团。最新的研究利用了人类、大猩猩和黑猩猩细胞培育的人脑类器官(Cerebral Organoids)来探索这一奥秘。研究发现,人类脑类器官之所以体积更大,是因为神经上皮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发生了形态变化,这一变化与细胞核的迁移以及细胞周期的延长密切相关(图11)。研究人员还鉴定出了一个关键基因——ZEB2,这是一种已知的上皮-间充质转化调节因子。通过调控ZEB2及其下游的信号传导路径,研究人员能够在人类脑类器官中诱导出非人类大猿的结构特征。这项研究确立了神经上皮细胞形态变化在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Benito-Kwiecinski et al., 2021),这个只是许多变化的基因里的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基因有人类特异性的变化尚未被详细研究。

图11. 由ZEB2基因导致的人类大脑的扩张机制。示意图总结了神经前体细胞在发育过程中的的形态变化。类人猿的前体细胞经历了从神经上皮细胞(NE)到过渡性神经上皮细胞(tNE),再到产生神经元的放射状胶质细胞(RG)的渐进式转变。人类与大猩猩的神经前体细胞的平均细胞周期长度分别为18.83小时和22.10小时。与类人猿细胞相比,人类细胞更晚地显示出过渡性神经上皮(tNE)的形态特征,这种延迟的转变与人类较短的细胞周期相结合,可能导致人类产生更多的神经元,从而解释了人类大脑扩张的机制。ZEB2作为这一转变的关键基因,通过与BMP(骨形态发生蛋白)信号通路中的SMADs蛋白质相互作用,下调神经上皮细胞的特征,特别是紧密连接蛋白(Tight junctions),并且通过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重组导致顶端收缩(Benito-Kwiecinski et al., 2021)。
4
演化的味道: 人类与黑猩猩分离之谜
嗅觉和味觉在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让我们能够感知周围的世界,还在生存、繁衍及社会交往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研究显示,嗅觉系统在生物演化的时间线上占据了极其古老的位置,甚至比其他感官起源都要早。在早期人类的生活中,嗅觉帮助我们的祖先检测食物的新鲜度与安全性、选择合适的伴侣,并且避免潜在的有毒物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存几率。与此同时,味觉通过舌头上的味蕾对食物进行安全性和营养价值的评估,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饮食偏好和习惯,并且与情绪记忆紧密相连。
通过对人类与猿类之间的遗传差异的深入研究,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理论,即人类与黑猩猩的分化可能与嗅觉和味觉系统的演变有关(https://news.cornell.edu/stories/2003/12/lifestyle-accounts-difference-chimp-human-genome)。研究团队发现,有数百个与嗅觉及消化功能相关的基因出现了序列变化。他们推测,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饮食方式转变所驱动的,这种转变进一步促进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分化。此外,这些基因的变化还影响到了长骨的生长、体毛分布以及听力发展,而听力的改进被认为与语言能力的进步有着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肉类消费的增加可能也减少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体力差距。
据灵长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大约19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从先前可能存在的多配偶制或某种形式的性别主导关系转变为一种更具合作性的模式。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男性与女性开始共享肉食资源,这使得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支持,从而促进了其体型的增长,进而能够孕育和分娩出拥有更大脑容量的后代。
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人类的演化是一个漫长且渐进的过程,每一步都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猿类到现代智人,我们不仅掌握了直立行走的能力,还逐步发展出使用工具、语言交流等复杂技能,最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社会体系。正是这些独特的适应性特征,使得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除此之外,人类与其他猿类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认知能力、代谢机制以及免疫系统的不同。这些差异使得人类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栖息环境,开发出非凡的技术,并重塑整个生物圈。
要理解人类表型演化的路径,关键在于探究人类与猿类基因组之间的异同。例如,尽管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序列仅存在0.1%的差异,但两者在基因表达和调控机制上的不同却是显著的,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在生理和行为上的巨大差异。将人类特有的遗传变化与物种差异联系起来一直充满挑战,这是因为存在大量低效应大小的遗传变化,对发育过程中细胞类型水平上的表型差异描述有限,以及缺乏实验模型。
展望未来,有三项关键技术的进步使得对灵长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变得更加可行:单细胞组学技术的发展,允许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观察细胞活动;使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来研究从少量组织样本中体外形成多种器官和组织的过程;以及创建复合细胞系和类器官的能力,这有助于模拟体内环境下的复杂生物过程。这些研究将揭示猿类与原始人类在分化过程中哪些特性是共有的,哪些则是各自独特的,最终为我们解开“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这一谜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参考文献:
1. Almécija, S., Hammond, A.S., Thompson, N.E., Pugh, K.D., Moyà-Solà, S., and Alba, D.M. (2021). Fossil apes and human evolution. Science 372, eabb4363.
2. Benito-Kwiecinski, S., Giandomenico, S.L., Sutcliffe, M., Riis, E.S., Freire-Pritchett, P., Kelava, I., Wunderlich, S., Martin, U., Wray, G.A., McDole, K., et al. (2021). An early cell shape transition drives evolutionary expansion of the human forebrain. Cell 184, 2084-2102.e19.
3. Boisserie, J.-R. (2010). Ardipithecus Ramidus and the Birth of Humanity. Ann. d’Ethiopie 25, 271–281.
4. Dominguez-Rodrigo, M. (2014). Is the “Savanna Hypothesis” a Dead Concept for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Earliest Hominins? Curr. Anthropol. 55, 59–81.
5. Garber, P.A. (1984). Adaptations for Foraging in Nonhuman Primates. In Contributions to an Organismal Biology of Prosimians, Monkeys, and Apes, P.S. Rodman, and J.G.H. Cant, e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12–133.
6. Kun, E., Javan, E.M., Smith, O., Gulamali, F., de la Fuente, J., Flynn, B.I., Vajrala, K., Trutner, Z., Jayakumar, P., Tucker-Drob, E.M., et al. (2024).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human skeletal form. Science 381, eadf8009.
7. Machnicki, A.L., and Reno, P.L. (2020). Great apes and humans evolved from a long-backed ancestor. J. Hum. Evol. 144, 102791.
8. Pilbeam, D., and Young, N. (2004). Hominoid evolution: synthesizing disparate data. Comptes Rendus Palevol 3, 305–321.
9. Pollen, A.A., Kilik, U., Lowe, C.B., and Camp, J.G. (2023). Human-specific genetics: new tools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asis of human evolution. Nat. Rev. Genet. 24, 687–711.
10. Potts, R. (1998). Environmental hypotheses of hominin evolution. Am. J. Phys. Anthropol. 107, 93–136.
11. Prost, J.H. (1965). A definitional system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imate locomotion. Am. Anthropol. 67, 1198–1214.
12. White, T.D., Suwa, G., and Asfaw, B. (1994). Australopithecus ramidus, a new species of early hominid from Aramis, Ethiopia. Nature 371, 306–312.
13. White, T.D., Asfaw, B., Beyene, Y., Haile-Selassie, Y., Lovejoy, C.O., Suwa, G., and WoldeGabriel, G. (2009). Ardipithecus ramidus and the Paleobiology of Early Hominids. Science 326, 64–86.
14. Williams, S.A., Prang, T.C., Russo, G.A., Young, N.M., and Gebo, D.L. (2023). African apes and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orthogrady and bipedalism. Am. J. Biol. Anthropol. 181, 58–80.
15. Wiseman, A.L.A. (2023). Three-dimensional volumetric musc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pelvis and limb, with estimations of limb leverage. R. Soc. Open Sci. 10, 230356.
16. Zhang, Y., Ni, X., Li, Q., Stidham, T., Lu, D., Gao, F., Zhang, C., and Harrison, T. (2024). Lufengpithecus inner ear provides evidence of a common locomotor repertoire ancestral to human bipedalism. Innov. 5.
17. Zhou, B., He, Y., Chen, Y., and Su, B. (2023). Comparative genomic analysis identifies Great–Ape–specific structural variants and their evolutionary relevance. Mol. Biol. Evol. 40, msad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