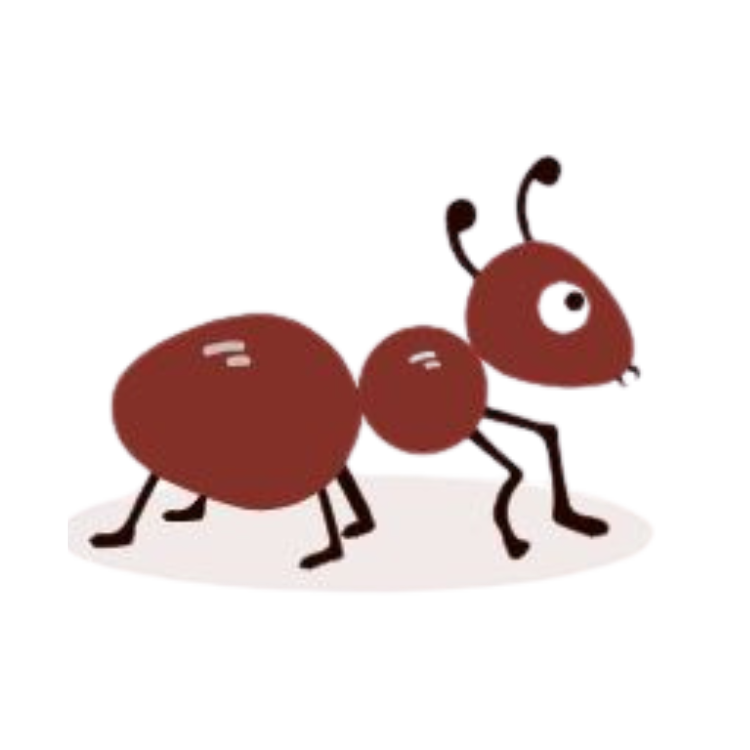呼吁生命科学领域统一使用“演化”指代evolution
“进化”和“演化”两个词都是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两者内涵上本应该是一致,即达尔文所提的物种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而逐渐变化的过程。但由于在中文语义上,“进化”带有定向性的进步含义,使得evolution的真正涵意被局限于具有明显方向性的演变。近日,生命演化研究中心的张国捷和孙仲夷在《遗传》杂志上刊文《为什么应该弃用“进化”而使用“演化”》,阐述两者的差别,说明“进化”一词不仅无法体现evolution的完整含义,而且其所产生的误解也会阻碍近几十年演化新理论的理解与传播。因此郑重呼吁生命科学领域内统一使用“演化”这一翻译,以提高科学传播的准确性。在此转发这一文章的原文。
“为什么应该弃用“进化”而使用“演化”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evolution”一词在主流的中文语境中被翻译为“进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进化”一词意指“生物从较低级、较简单的状态向较高级、较复杂的状态演变”。这里还包含了“生命系统的复杂化是一种普遍的自发趋势”的认知。然而出于对“进步性”这一核心语义的质疑,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提出应该使用“演化”这一翻译才符合生命演化的客观规律和演化论(即对于所谓“进化”和“进化论”,后文都采用“演化”或“演化论”)的基本逻辑。对“进步性”看法上的分歧使得“evolution”一词的翻译应保留为“进化”或改为“演化”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1~3]。尽管有些学者也建议应该使用“演化”[4],但仍有些人认为“进化”一词已经沿用很久,其标准定义就是达尔文的演化理论,然而从日常实践和交流上来看,极大比例的未受过系统演化理论训练的人,对“进化”的理解并不很准确。对于公众,在面对“进化”一词时,容易望文生义,从字面上以进步和迭代的视角来理解生物演化过程。而近年来,更有部分学者在科普作品中表示支持“进化”这一翻译[5,6],其核心观点是,生命演化过程中确实存在进步趋势,生命演化由适应性不断提升的单向“进步”趋势所主导,这种进步观念来源于他们对姊妹群之间展示的性状差异,乃至生理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程度差异的理解。本文将从多个方面系统性反驳这一观点,并指出“进化”这一翻译在语义上已经大幅度偏离了学科的思想内核,不仅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给大众带来有误解的暗示,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对相关新理论的思考和探索。因此我们强烈支持“演化”的翻译方式,特别在专业领域内应该弃用“进化”的翻译。
01 “evolution”翻译的分歧来源

从直观上讲,“进化”一词包含着“朝着某种更高级更进步的方向不断变化”的语义,但这并不是中文语境独有的理解方式。在过去相当长时间的英文语境中,“evolution”事实上一直都代表着这种“进步发展”(progress)的含义[7]。在前达尔文时代,人们普遍相信自身物种是一切客观事物变化的终极形态,高于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以至于早期版本的“进化论”将生物的谱系关系描述为以人类为终点的单向序列,即直生论(orthogenesis)。达尔文在编写《物种起源》时,将生物演变过程描述成“有修饰的血统继承(descents with modification)”。英文将“evolution”一词等价于达尔文所指的演化的含义最早能追溯到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1867年发表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一书[8]。总之,对于“evolution”一词,西方科学史本就深刻反映了其在语义上从“进化”到“演化”的理解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理解方式的转变并没有随着对达尔文等著作的翻译而完整传到中国。今天中国的演化学者们普遍认为,“演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著名的爱国进步学者严复在翻译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1893年罗曼尼斯讲座的补充讲稿《演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时,创造性地将书名译为“天演论”。在很多人看来,“evolution”最初被严复翻译为颇有“演化”意味的“天演”,而“进化”的翻译则在20世纪初受日本翻译影响所引入的。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最早使用“进化”一词的文献也是《天演论》,其卷下论第17篇的题目就是《进化》,但该篇内容与生命演化无关,讨论的是社会治理[9]。总的来说,我们看待演化论传入中国的历程时不能忽视其时代背景,严复的《天演论》以及1902年马君武对《物种起源》的翻译主要都是出于救亡图存的想法而组织起来的。他们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来阐述“落后就要挨打,必须主动变革”的观点,因此最初传入中国的演化论体系很大程度包含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以及译者本人的理解[10]。现在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生物从没有落后与先进的差别,只要能适应生存环境,哪怕像蓝藻那样简单的单细胞生命形态也能在地球上维持几十亿年。只有放到技术与工程领域,在技术发展和产品设计中,经常使用“进化”来描述产品或者技术的更新迭代。在生物学知识的传播过程中,“进化”一词很容易让大众曲解达尔文的思想内涵,加重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经过了近两百年的系统性发展,今天的演化生物学已经构建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尺度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更加丰富了对演化问题的理解。我们接下来会从多方面阐释,像“进化”这样受制于历史局限性的翻译方式及其对公众所阐述的误解已经严重背离了当今学界对生命演化的基本共识和新的认知。
02 对演化方向性的认知变化

理查德·道金斯的《盲目钟表匠》
要讨论两种翻译方式带来的分歧,必须首先从生命演化的方向性谈起。自达尔文时代以来,人们便不再承认生命演化有从“简单低级”状态朝着“复杂高级”方向演变的固有趋势。但很多人将“进化”所包含的“进步性”概念解释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提升的适应性优势。携带有益突变的个体在种群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直到该表型被基本固定下来。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使得生物在种群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累积优势性状,“进步性”指的就是它们在特定环境下比某个阶段的祖先有更强的生存繁殖能力。如果从微观到宏观的演化过程都被这个逻辑所主导的话,“进化”这一翻译似乎可以接受。接下来我们需要梳理这种认知在历史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如何受到新的实验证据的挑战。
在20世纪40年代起,学界将达尔文演化理论及孟德尔遗传学进行了综合,提出了现代演化综论(Modern Synthesis),并进一步统合了多个生物学分支,形成了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后者在20世纪70到80年代进一步吸纳整合了分子演化理论的架构,成为当今主流的经典理论。其中,日本学者木村资生(Kimura Motoo)和太田朋子(Tomoko Ohta)等的中性演化理论(Neutral Theory)在分子演化上修正了人们对于演化的方向性的部分理解[11]。他们基于大量基因序列比较的结果指出,基因组上的大多数突变都是中性或者接近中性的,并不带来显著的适合度差异(非有害或者有利),因此人们观察到的基本稳定的基因组序列大多是被遗传漂变等随机因素所固定下来的。考虑到分子演化理论的补充,新达尔文主义的主流观点是,突变和重组提供了演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主导了演化的方向,而遗传漂变对演化的结果产生随机影响(主要是对中性变异的固定,例如同义突变)。
对自然选择重要性的最经典论述莫过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达尔文在此书的第5章末尾阐述了一个核心结论,其原话是“子代与亲代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每一差异必有其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与物种习性相关的或构造上重要的变异,都是有利变异缓慢累积而形成的”[12]。在达尔文本人的叙述逻辑里隐含着演化的渐变论假设,认为自然选择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持续主导演化方向。在新达尔文主义视角下,有利突变的累积过程表现为特定的选择压力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步固定每个等位突变。比如,在适应特定环境的过程中,某个种群的祖先基因型aabbcc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先逐渐被AAbbcc取代,然后AAbbcc再被AABBcc取代,最后被替换为能稳定适应当前环境的基因型AABBCC。按照这样的逻辑,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所有复杂生物性状的形成过程都想象为使其获得某种核心的适应性功能(例如视觉、登陆、飞行、智力等)的单调递增的连续变化过程。其在《盲眼钟表匠》一书中这样说道,“按顺序‘进化’到拥有当前人类6%视力状态的祖先一定比5%时的更好,因此无数微小的有利突变逐步取代旧的表型,一个复杂的器官就这样在漫长的连续演化步骤中诞生”[13]。如果一切显著的表型差异都需要这样一个连续替代的变异序列的话,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特定“进步”方向的长期过程称为是“进化”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真实的演化过程中并不像渐变论假设所预想的那样由单一适应性长期主导宏观演化方向。从分子演化的角度看,人们在对大量物种的基因组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新物种的出现往往不是靠缓慢积累被自然选择固定下来的随机突变而逐渐实现;事实恰恰相反,跨种杂交、渐渗、不完全谱系分流、基因组重排等带来大规模基因组变异的机制往往对物种形成及形态演变做出了关键贡献[14~16]。而从形态演化的角度看,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尼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根据大量化石证据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即古生物的形态演化过程主要是由漫长的徘徊停滞和相对十分短暂的形态骤变组成[17]。当分子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技术手段足以分析宏观演化的更丰富细节时,人们就会意识到渐变论所预想的那样一条稳定而持续的宏观演化轨迹并不存在。例如,面对现生长颈鹿物种的修长脖颈,我们既不能预测一百万年以后,长颈鹿脖子还会不会继续变得更长,也无法断言过去每一阶段的长颈鹿祖先种群中,脖子更长的个体必定获得了更大的生存优势。
现存生物物种的一部分表型确实可以找到适配其当前生存环境的、明显的适应性优势,但我们不能默认大多数特征的形成必须靠长时间持续不断地取代和淘汰过渡表型才能实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胚胎发育机制的深入研究让人们对形态演化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以著名的加拉帕戈斯地雀为例,勇地雀(Geospiza fortis)和大嘴地雀(G. magnirostris)拥有宽厚的喙,十分适合用来啄碎种子外壳;而仙人掌地雀(G. scandens)等则使用它们细长的喙来啄取果子和花蜜。其中,大嘴地雀等的宽喙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喙发育的初始阶段单个基因(Bmp4)在上喙间充质处表达量的微小提升,而仙人掌地雀的长喙主要来自钙调蛋白CaM在喙发育早期的表达量提升,且这些表型变化可以在鸡胚实验中验证[18,19]。也就是说,作用在胚胎期个别关键基因(例如形态发生素)表达水平的微小变化足以直接带来成体水平的显著表型差异[20]。故后者的形成往往并不需要无数微小的有利突变的缓慢累积,胚胎发育的异时性使成体表型在演化中呈现为不连续变化的现象比比皆是[21]。按照达尔文预想的情况,例如喙的显著形态变化需要多个变异的累积,那么一只大嘴地雀持有稍微变窄的喙的形态就会对其啄击种子产生小的不利,这种违逆该物种固有演化方向的变异就更容易被淘汰。但如果存在能显著改变喙形态的遗传变异的话,持有这种变异的达尔文雀个体很有可能直接脱离其亲代的食性偏好,受到与其他个体不同的选择方式所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生存环境的自然选择对某些特定表型的影响十分显著,例如工业革命时期在英国曼彻斯特普遍被工业废气熏黑的墙面和树干对尺蠖蛾颜色的选择。然而在大多数不那么极端的一般情况下,自然选择对多数等位基因未必能够施加十分严格且专一的限制,使之稳定收敛到唯一的最适状态,而种群内持有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完全可以根据自身表型开辟出多样的生存策略,比如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自身的食谱偏好性,这使得某些遗传特征的多态性可能在种群内长期维持。对于无数具体的一般表型,我们无法逐个证实它们究竟是基于何种具体的适应性优势或是其他机制而被固定了下来,尤其是在面对具体的数量性状时,我们很难从原理上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前阶段的某个稳定数值必然优于比它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故而“所有稳定的可遗传表型都能被解释为某种特定环境下的最佳适应方案”这一观点无法在任意情形下都具备普适的可证伪性。因此,使用“进化”这一概念就只能概括某些受特定生存条件严格限制的极少数特征的演化趋势,例如抗生素环境下细菌抗药性的不断提升。虽然我们承认自然选择和生命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无处不在,但绝大多数生物特征往往并不沿着一条让特定适应能力持续提升的固有轨迹演化下去,并逐步趋向于收敛到某个最能适应特定环境的全局最优解。演化除了有遗传多态性收敛的趋势之外还有遗传多态性发散甚至大幅度扩张的趋势,即辐射演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03 对生命演化复杂性的全新理解

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
在对演化的方向性进行讨论之后,我们还需要从生命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角度阐述为什么要放弃“进化”的翻译。正如我们在上文论述过的,“进化”这一翻译承载了主流学界对自然选择的适用性的严重高估。20世纪80年代之前,演化学界曾广泛存在选择主义(selectionism)观点,强调种群中固定下来的大多数突变都是有益的,或者至少与大量发生的有益突变有关[22]。当时的多数人看来,只要演化的时间足够长,繁多的适应性累积就足以让生物的基因型和表型变得面目全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演化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就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除非是在非常近缘的物种之间,否则寻找同源基因几乎是徒劳的[23]。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对于形态复杂多样的后生动物(Metazoan),它们都是用同一套发育调控基因集合(genetic toolkit)来编码出多样的形态和精细的组织结构,这完全背离了选择主义者预想的情况[24]。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同源性概念理解的更新如何改变现代演化综论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认知。
对于眼睛、大脑等复杂组织器官的演化起源问题,现代演化综论曾提出过一种主流解释,即新结构源自旧结构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特定的新功能[25]。受选择主义思想的影响,新特征的演化起源曾被归因于祖先物种所经历环境的特殊性,即所谓的生态机遇(ecological opportunity)[26]。例如,人们曾在过去普遍相信,复杂的生存竞争和捕食压力使得不同动物祖先的感光能力需要得到不断提升,直到最后“进化出了”有视觉成像功能的眼睛。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类似的环境很容易使得不同物种发生趋同演化,例如典型的北极哺乳动物普遍具备的白色外观使它们更容易融入白雪覆盖的环境中,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因此他们推测,不同门类动物的生理结构复杂化也是由适应特定环境所驱动的。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发育生物学实验证据表明,全新结构性特征的出现实际上与生态机遇没有必然联系,是产生了特殊的遗传变异而非适应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们的演化起源[27]。
由于在不同门类的动物之间很难直接找出一致的解剖特征,于是在此前的一百多年,人们普遍相信,不同门类的相同功能的组织器官都是各自独立起源,在功能上展示出趋同演化[24]。例如,迈尔曾认为眼睛或许曾独立出现了40余次[28],迥然不同的基因复合体也能提供相同的生物学功能。但事实上,人类、果蝇、章鱼、乃至于箱水母的眼睛都是由同一套分子调控机制激活最初的发育过程,这种基础发育能力是继承自共同祖先的同源性状,并不像迈尔所猜测的“条条大路通罗马”[29]。除此之外,心脏与肌肉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也都能在相隔遥远的动物门类中找到高度类似的发育调控机制,它们应该被解释为祖征而不是由适应类似环境带来的趋同演化的产物[30-32]。至少能追溯到一个或多个门类动物祖先阶段并维持了5亿年以上的超保守发育调控模式在动物演化过程中十分常见,这种由系统发生关系而非自然选择所支配的宏观演化规律被称为深度同源性(deep homology),是支持演化论最核心的共同祖先假说的有力证据[33]。
对于多细胞动物而言,任何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和生理结构都不是贯穿生命周期始终的静态特征,而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弄清个体发育过程中各种表型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解决复杂性状起源与演化问题的关键。奥地利演化学家鲁珀特·里德尔(Rupert Riedl)最早提出,极少数关键特征(例如胚层、体轴、脊索等基础结构)在演化中首次出现为更多复杂多样的下游特征提供了发育的前提条件;而在此后的演化过程中,无数下游特征的累积又加重了这些上游特征的负担,将它们固定为高度保守的躯体架构(body plan)[34,35]。里德尔的学生们进一步指出,全新的结构性特征起源于特定的演化阶段,它不是由更早祖先阶段的其他特征在适应性提升的过程中逐步转化而来的,而是某个特定类群的共同祖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胚胎发育能力,即演化创新(evolutionary innovation)[36,37]。美国分子发育学家埃里克·戴维森(Eric Davidson)等则在分子层面系统性阐述了演化和发育的关系:细胞分化的发来自于对特定基因调控网络(gene regulatory network,GRN)的激活,网络上游保守调控关系的建立使得某种特定的躯体架构在演化中首次出现并维持保守[30]。古尔德指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眼睛能为动物带来如此巨大的生存优势,于是许多门类的动物就都能纷纷独立地‘进化’出了眼睛。然而,失去了Pax-6编码的基因结构(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所有产生眼睛的合理可能性都可能消失,但保留这些发育途径的谱系可以继续演化,并将视觉器官排列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功能”[38]。
思想层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促进了演化发育生物学(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evo-devo)理论的提出。在evo-devo看来,新达尔文主义体系更多的讨论建立在既有生理结构基础上的某些修饰性特征的演化(例如颜色、形态、大小等方面的变化),而无法解释全新特征的演化起源问题[39]。后者需要从个体内部不同模块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因间调控关系,细胞之间的诱导分化等)方面得到解释,即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演化体系[40]。选择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从适应性外因还是结构性内因出发来分析演化,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内核[41]。Evo-devo有效弥补了经典理论无法适用于宏观演化领域的局限性,从事evo-devo理论研究的多数学者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将自身与新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来构建一套新的更加完善的演化理论体系,即拓展演化综论(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EES)[42,43]。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进化”这一翻译所包含的“定向进步”思维对宏观演化中的许多关键过程的解释都带来了巨大的曲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错误解读。寒武纪大爆发对后生动物演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无需在此赘述。不同动物门类躯体架构的都集中在寒武纪前后的数千万年时间内出现,而在此阶段内为何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多样的动物形态曾一度困扰达尔文以来的许多代演化学者。很多人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当时环境发生了某些特殊变化,例如氧气浓度提升的“大氧化”事件或地磁场的骤变等,或者复杂捕食关系的建立使得多细胞动物在“军备竞赛”中实现复杂性的提升。这些事件的确发生在寒武纪大爆发所处的时期,但却不能跟如此超大规模的辐射演化建立任何有效的因果逻辑。只有当人们摒弃选择主义的限制,关注到躯体架构的形成机制才能解释这个关键现象。例如,任何环境的特殊性都无法有助于解释脊索动物的祖先具体如何在这一阶段产生了脊索和背神经管的结构。而在对大量跨门类物种的胚胎发育过程进行比较之后,人们发现两侧对称动物具备的三胚层、二体轴、施佩曼组织者细胞等一系列基础发育特征都能在刺胞动物的原肠胚中找到同源模式[31,44,45]。所以,原肠胚发育模式的建立才应该是推动寒武纪大爆发的关键,不同门类动物之间躯体架构的多样性则源于对一系列共有的基础发育模式的修改和调整[46]。只有从胚胎发育模式的同源性出发,才能将复杂性状起源问题解释清楚,如果总是先入为主地把远缘物种之间类似的生理功能归结为特定环境带来的趋同演化,那么连最核心的共同祖先假说也会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在evo-devo的研究中,人们更关注具体的系统发生关系(包括识别祖征或衍征、单系群或多系群)而不是抽象的群体遗传学模型(例如计算适合度以及有效种群规模的变化),其中鉴定同源性(主要包括基因同源性和细胞类型同源性)是展开一切分析的基础[47]。
总之,evo-devo为复杂性起源的解释提供了具有生物学基础和可实验操作的解释。结构性创新是生物可以在新的领域提升适应性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只有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基本眼睛结构的动物,才有机会提升视力。但选择主义者则将生物复杂性的提升解释为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提升,以及种内或种间竞争关系能够驱使着某些核心性能不断进步提升,例如他们普遍认为对视力提升的需求会促使不同动物门类分别独立“进化”出越来越复杂的眼睛。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弄反了最基础的因果逻辑,于是得出了大量被后续实验证伪的错误认知。因此,将“evolution”翻译为“演化”有助于扭转过去一百多年内极端的选择主义者们对于生命复杂性演化的错误认知,这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对演化生物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04 从演化潜力(evolvability)的角度解释辐射演化

图片借鉴自Kurochkin and Bogdanovich 2008。鸟类羽毛产生的可能演化路径:I和II,简单的羽毛可能对温度调节或性选择中个体展示起到重要作用;III随着树栖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加,身体羽毛可能为鸟类祖先提供了更具空气动力学形状,有助于在树枝间跳跃;IV和V,前肢上的简单羽状羽毛可能允许降落伞式滑翔;VI,具有对称羽片的较大羽状羽毛可能允许滑翔;VII,不对称羽毛可能有助于更高效的滑翔;VIII,真正意义的动力飞翔。
4.1 演化潜力概念对完整演化论的必要性
从个体水平看,具体遗传突变的产生可以被视为纯随机事件,弄清楚某个遗传突变如何产生某种表型变异就可以把一个遗传学问题解释清楚(例如解析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遗传机制)。虽然我们无法具体预测每个单独的碱基突变是否发生,但考虑到一个独立性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许多遗传变异的参与,我们仍可以从中归纳出适应性性状潜在的多态性分布方式来摆脱单个突变的随机性为演化研究带来的不可知论。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个种群或物种类群可能在哪些特征上相对更容易产生供自然选择作用的表型多态性,其中也包括多个特征组合的可能性分布情况,这就是演化潜力(evolvability)。对大多数哺乳动物统计其四肢内各个骨骼的长度分布后就会发现,左前肢或右前肢内对应的两个骨骼长度呈现出极高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它们的发育过程被完全一致的基因调控程序所控制;而前后肢对应骨骼之间的正相关程度略弱于左右是因为它们的发育调控模式略有小幅度差异[48]。也就是说,哺乳动物有机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前后肢形态差异供自然选择作用,例如蝙蝠上肢的部分指骨大幅度变长形成有飞行能力的翅膀;但它们对应的左右肢之间则几乎无法产生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形态差异,这种演化潜力的差异使得前者可以作为演化的原材料但后者不行。不考虑演化潜力的影响就很容易得出“哺乳动物呈现出左右肢体的对称性是因为不对称的个体全部被自然选择淘汰”这种错误的结论。缺乏演化潜力这一核心概念,而只是泛泛地讨论作用在随机突变上的自然选择就会使得现代演化综论不能对普遍的演化现象给出足够清楚的解释。只有将演化潜力纳入演化论中,才能将影响演化的内外因素综合起来,系统性地解释演化的发生。单方面强调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进步”就会使人们很容易陷入环境决定论的严重误区之中,这也是我们极力呼吁使用“演化”这一概念的另一重要原因。
4.2 演化潜力概念对完整演化论的必要性
虽然人类是“最高等”物种的错误认知在科学界已经不再被承认,但是一些人将一对姊妹群之间客观存在的物种多样性差异视为“进步性”的体现[5,6]。这种观点首先强调了“进步”的相对性只有放到姊妹群之间比较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有颌脊椎动物(Gnathostomata)在物种多样性上显著多于无颌脊椎动物(圆口纲)(Cyclostomata)、四足动物(Tetrapods)的物种多样性显著多于肺鱼(Dipnomorpha)和腔棘鱼(Coelacanth)等现象被视为由“适应性进步”的差异导致的。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到,物种多样性的变化是动态的,某个庞大的类群内部的不同分支在不同地质年代中可能有巨大差异,例如现生的头足纲软体动物(Cephalopoda)的多样性主要由蛸亚纲(Coleoidea)所贡献,但该类群在古生代最繁盛的则是鹦鹉螺亚纲(Nautiloidea),该如何定义哪一支更加“进步”?另外,只有发生了辐射演化的类群才可以显著体现出自身相对于其姊妹群的明显“进步”趋势,因此由多样性差异体现出的“进步”只代表生命演化中的特殊情况,不具备普适性。更重要的是,例如所谓有颌动物相比于圆口纲的“进步性”只有在二者分岔节点处才能有效定义,它不能向下传导,也就是说这种整体水平的“进步性差异”不能对解释任何脊椎动物种群的适应性提供帮助。因此,这种基于姊妹群之间物种多样性差异所定义出的“进步性”与任何其他演化生物学概念都无法建立有效联系,所以它是个毫无科学价值的孤立概念,用它来解释辐射演化也只会陷入到循环论证的陷阱,无法得到任何有效结论。
辐射演化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全新的适应性方式的出现,但这并不是“适应性进步”的必然产物,而是全新结构特征出现带来的演化潜力。鸟类早期辐射演化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过去很直接将其简单归结为占据天空生态位带来的适应性优势。但当我们讨论起鸟类如何获得飞行能力时,就会找到飞羽的形成、翅膀的结构、中空的骨骼、发达的龙骨突等多个主要方面。在这些条件中,羽毛的形成无疑是最特殊也是最关键的,因为其他结构都能从它们的爬行动物近亲体内找到同源的组织器官,可以解释为已有特征的形态转变,而羽毛似乎跟爬行动物的表皮鳞片在成分和结构上都存在巨大差异,难以被视为同类事物。中华龙鸟(Sinosau-ro¬pteryx)等某些类鸟恐龙具有原始的羽毛结构,但完全不能飞行,这说明早期羽毛结构与飞行起源没有直接关系,而被认为具有保暖或展示等其他功能[49]。因此,预适应模型将此解释为不同的适应过程带来了功能上的转变。但已有充分的发育生物学和化石证据表明羽毛的起源不能解释为继承自更早祖先阶段旧有皮肤结构的形态转变(祖征),而是涉及在鸟类起源过程中依次建立的一系列鸟类特有的皮肤发育调控机制(衍征)[50~52],其特有的组织结构与爬行动物皮肤鳞片并不同源。具体来说,鸟类体表的飞羽、绒羽、纤羽等不同类型的羽毛是在不同皮肤区域的皮下真皮层细胞差异性地诱导表皮细胞分化而形成的[53]。表皮细胞成分的异质性为鸟类羽毛带来了结构的复杂性和功能的多样性。其中对飞行至关重要的正羽是拥有羽轴、羽枝、羽小枝、羽小钩等精细结构的复杂组织,需要在多种不同的发育信号对真皮和表皮细胞的一系列有序诱导下才能形成[51]。其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添加新的发育调控机制所带来的一对多细胞分化过程,而不是适应飞行使鸟类羽毛逐渐由原始简单结构转向复杂结构的一对一转化过程。
对鸟类演化而言,羽毛的出现源于表皮细胞分化方式的创新,并为其适应更广泛生存环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如果鸟类祖先未曾获得过相应结构的发育能力,它们就没有适应飞行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新结构出现所带来的演化潜力提升了适应性景观的维度,让环境在更高维度的表型分布空间中起选择作用,由此诞生了适应全新生态位的潜在可能(下图)。我们必须理清其中的逻辑关键:重大结构性创新是产生全新适应性优势的前提条件,而非“适应性优势提升”促使全新结构形成。相对于“进化”,在语义上不携带“适应性进步”含义的“演化”能更好地反映这一过程。虽然生命体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随时间累积确实存在,但复杂化并不是生命演化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极端罕见的演化创新事件所释放出的演化潜力推动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地球上绝大部分生命体都将继承自LUCA (The Last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的单细胞形态维持了几十亿年,在细胞形态上而几乎没有任何显著的复杂化趋势(真核生物的出现可以被视作一次极其偶然的演化事件)。生命复杂化既不是自发的普适规律,也并非由代表适应性优势提升的“进步性”所推动,这与“进化”这一翻译方式所阐释出的语义具有重大分歧。

演化创新带来适应性景观维度的提升
一旦我们意识到生命演化存在形态多样化的潜力,就不能将演化简单理解为某个新表型逐步替代旧表型的单向“进化”序列。像四足动物从海洋登陆,或者鸟类获得飞行能力这样的重大宏观演化事件都由一系列复杂步骤组成,但我们不能认为其中的每一步骤都是为最终演化结果积累优势才会得以保留,而在此过程中没有“实现最终目的”的过渡物种都会因此被逐渐替代或最终淘汰。例如,作为四足动物的近亲,腔棘鱼和肺鱼保留了肉鳍鱼祖先阶段的某些关键特征及发育调控网络,其中四足动物的爪和趾头都能在腔棘鱼中找到同源结构[54]。虽然这些特征被证明是四足动物最终实现登陆结果所必需的,但它们起源于肉鳍鱼祖先阶段,有些甚至起源于硬骨鱼祖先,远早于四足动物诞生[55,56]。在自然演化中,如果我们把多个独立性状的依次累积过程视为朝向特定结果(例如最终实现登陆、飞行或视觉成像)的“适应性进步”,就不得不预设一个“最终目标”来解释该结果实现之前的漫长演化过程。但这就等于把演化论彻底推向对立的智能设计体系中,因为只有智能行为体才会为了在将来实现特定目的而提前采取行动。如果单一目的论的方案失败,选择主义者又会通过预适应理论在它前面安排其他“目的”来维持其叙事逻辑。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为辐射演化或复杂性状起源预设任何特定类型的适应性优势,新结构的出现最初只是提供了适应全新生存方式的潜在可能性,它可以让不同后代在后续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被固定为不同的具体表型。例如有颌脊椎动物祖先获得最基础的四肢发育能力让不同后代能发育出鱼的鳍、爬行动物的爪、鸟的翅膀或人的手臂,这种上游发育功能不是专门用来应对某种具体环境而出现的。因此,今天的有颌动物在物种多样性上显著领先于其姊妹群圆口纲,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有机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形态多样性,并在更广泛尺度下受自然选择影响,并没有任何“适应性进步”水平的差距让每种圆口纲动物变得比有颌脊椎动物更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而趋于萎缩。
当我们抛弃有目的论内核的“进化”表述,就会认识到,辐射演化是一个涉及形态多样化的发散性过程,它不能被一条使特定适应性连续提升的单向轨迹(即上文介绍的,道金斯设想出来通过依次替代来实现的单向渐进过程)所概括。因此,若抛开演化潜力在宏观演化过程中扮演的关键作用,把姊妹群之间的表型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简单地归结为“适应性进步”水平的差异,事实上是在变相支持“脊椎动物比其姊妹群文昌鱼更加进步高级”等这一类直生论观点体系,这是演化生物学所一向反对的。伴随着我们对于演化潜力这一核心概念的深入研究,在今天使用“演化”的翻译方式来替代“进化”势在必行。
05 演化的副产物及权衡(trade-off)的结果

带有“适应性进步”语义的“进化”翻译也无法解释演化过程中的多效拮抗和权衡现象。生命演化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除了自然选择的外因之外,人们在过去半个世纪逐渐意识到必须把个体内多个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也考虑进来。如果特征A与特征B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当特征A产生某种变化时,特征B也要随之联动变化,但单独观察B的变化本身可能找不到什么明显的适应性提升,这种被连带着产生的性状变化被古尔德称为“拱肩”(spandrel)[40]。在古尔德看来,先入为主地将复杂有机体拆分成一个个单独性状,再逐个为它们讲述一个适应性故事往往会误入歧途;我们必须从有机体的整体性出发,将诸多性状联系起来分析哪些表型变化是适应带来的直接结果,而哪些则是因连带关系诞生的副产物。例如,人类的血液呈现为红色并不是因为红色本身比其他颜色更加适应环境,而是由于亚铁离子对于人类血红蛋白的氧气运输功能必不可少,其让血红素呈现红色只是依附在关键适应性特征上的副产物,即“拱肩”。
考虑到个体内的复杂关联,某个关键的适应性表型一旦产生变异就可能会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方式进一步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演化过程中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就很容易带来这种效果,其对人类演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距今约2万~8万年前,智人群体经历了一场关键的累积技术进化(cumulativ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CTE,根据语义特将此处翻译为“进化”),而高水平的社会容忍度成为高人口密度生活及合作化行为的必要先决条件。在此期间,睾酮激素分泌水平的降低更有利于提高宽容度而降低对抗性,进一步有利于复杂社会分工的出现,这一点可以从智人祖先颅面特征变得更加女性化得出,但除了最核心的适应性优势之外,睾酮分泌降低还带来了许多其他副产物,例如智人的上面部骨骼相对缩短导致下颌相对外凸,这形成了现代人类独有的下巴颏结构[57]。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类下巴颏是在儿童发育到成年的过程中,因不同面部区域发育速度差异而拉伸出来的结构,排除了其可能起源于对咀嚼等机械动作的适应[58]。
如果将视力、听力、运动能力等各方面的持续提升描述为带来生存优势的“进步性”的体现,那与之对应的“退化”现象往往被解释为原本的优势性状在某些选择放松的条件下不再具备优势,例如洞穴鱼类对于视觉能力的依赖大幅度降低使得盲眼性状得以保留。虽然从单独性状的适应性出发也能解释某些特定的“退化”现象,但当我们跳出仅分析单独性状的局限,从有机体的整体性出发考虑生命演化,就会发现多性状之间的权衡(trade-off)才是演化的常态。这能帮我们解答为什么许多给人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的疾病没有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被清除或被压低到一个极低的病发率水平。例如现代人类固定下来直立行走的基本方式之后,许多骨关节因此承受了比过去大得多的压力,这导致人群中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等疾病的发生率长期居高不下[59]。这是重力作用到人类现有身体结构的直接效应,无论适应性如何改变都无法消除重力等基本物理规律对人体的影响。相比之下,恶性肿瘤更加致命却也在人群有着极高的发病率,它的保留在过去只能被“选择阴影”(selection shadow)模型所解释,即过了个体繁殖高峰期之后自然选择的影响会越来越小[60]。然而,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清楚恶性肿瘤的普遍发生。肿瘤强大的迁移侵袭能力并不是体细胞突变带来的新事物,而主要是重新调用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广泛使用的上皮-间充质转换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间充质组织侵袭性的演变同时影响胎盘对母体的侵袭和癌症细胞对其他组织的侵袭能力[61]。在人类的胎盘中,上皮外滋养细胞(extravillous trophoblast cells, EVTs)是最具侵袭性的细胞类型。随着EVTs最近在类人猿中快速演化,子宫内膜基质也可能提高了免疫耐受力,以降低对胎儿滋养层细胞的抵抗性,从而增加了胎盘的可侵入性。相比之下,牛、马等丧失胎盘侵入性的有蹄动物,其肿瘤的恶性程度同样远低于人类[62]。也就是说,人类相对易患恶性肿瘤本身并不是优势性状,其很可能是在人类维持自身繁衍时不得不面对的客观风险。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生命演化并不能以任意形式去寻求理想情况下的各方最佳形态,许多表型的出现往往是在身体结构的系统性限制下别无他选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每个生物特征都能独立“进化”出完美的表型,那么各种疾病或者看似不完美的“退化”现象则变得难以解释,只站在有机体的整体性视角,我们才能理解特征之间的权衡能让任何局部特征都难以在演化过程中到达某种无可挑剔的“完美结局”。
06 结语
当我们回顾对“进步性”的批判时,一个无法忽视的人就是古尔德,他全方位否定了生命演化在任何意义上存在“进步性”[6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演化”与“进化”所代表观点的激烈争论也主要围绕着古尔德的观点所展开[64]。古尔德最早提出宏观演化无法用等位基因连续替代的群体模型简单外推而得出[65],并系统性批判了几乎完全由“选择导致适应”这一逻辑主导的选择主义思想[40]。更重要的是,他率先提出建立新达尔文主义之外的演化论逻辑的可行性[66],用结构主义体系引导了过去30年的理论创新方向[67]。Evo-devo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对生命复杂性的演化有了系统性解释,并强有力地回应了所谓“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等一系列对演化论最尖锐的质疑。演化发育生物学今天的成功离不开古尔德的奠基性贡献[21]。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翻译的争论背后是对生命演化理解方式的区别,它体现在对生命演化底层逻辑的阐述上,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绝不是咬文嚼字的口舌之争,如今这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科学理论问题。最近30年,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技术革新带来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让我们对于生命演化产生了新的思考[68]。在今天看来,所谓“适应性提升带来的进步性优势主导了生命演化的宏观趋势”这一陈旧观念已经被最近几十年的大量科学实验所充分否定,生命演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规律迫使我们必须放弃“进化”所代表的选择主义逻辑,而应该去使用没有方向性含义的“演化”。
总之,在对演化规律的理解不足的情况下,公众会将适应性逐渐提升的“定向进步”等同于生命演化过程,并因此接受将“evolution”一词在生命科学领域翻译为“进化”。即使放眼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仍有相当比例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地受直生论的影响,默认脊椎动物或哺乳动物特有的某些生理机制相对更“高级”,并有可能把这类偏见不经意地带到科研或教学工作中。对于他们感兴趣的具体科学问题,也许有更理想的非模式生物作为研究对象,但未被重视。且这种“进步性”认知很容易为演化论带来有目的的论述逻辑,并且阻碍了的对于复杂性状的演化起源、辐射演化的发生、疾病的长期演化等诸多新方向的探索。从各个方面来看,错误的翻译带来了许多严重背离理论核心思想的重大歧义,也将阻碍新的演化理论的传播和发展。考虑到演化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多尺度非定向过程,因此我们郑重呼吁在生命科学领域以“演化”取代“进化”的翻译。
致谢
诚挚感谢EES理论的主要提出者,美国耶鲁大学演化与生态学院Günter P. Wagner教授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康德拉·洛伦茨研究所Gerd B. Müller教授在与作者就演化理论创新等相关问题深入探讨过程中给予的广泛启发和支持鼓励,这有效地帮助了作者在本文表达出较为完整的观点体系。
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可查看《遗传》杂志原文。《遗传》是由中国遗传学会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精品学术期刊。1979年创刊,至今已有40余年历史,在国内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领域具有着广泛的读者和较高的影响力。目前,被国际和国内多家权威数据库收录,如PubMed、Medline、Scopus、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CSCD等,并多次荣获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等称号。
欢迎关注!www.chinagene.cn
参考文献
[1]田洺. 进化是进步吗?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6, (3): 71–75.
[2] 张伯剀. 进化=进步? 大科技·科学之谜, 2006, (12): 22–24.
[3] 李建会. 进化不是进步吗?——古尔德的反进化性进步观批判.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 (1): 3–9
[4] 顾红雅. 有关Evolution的中文翻译. 植物学报, 2015, (2): 148–148.
[5] 卢平. “进化”还是“演化”?关键在于尺度. 科普中国网. (2023-08-17).
[6] 曾刚. 听说, “进化”这个词不能用了?科普中国网. (2023-07-09).
[7] Gould SJ. Ever Since Darwin: Reflections on Natural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8] Spencer H. First Principl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7.
[9] Geng ZC. Thought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 Sci Technol Rev, 2000, 18(12): 8–11.
庚镇城. “Evolution”一词译成“进化”及其传入中国的经过. 科技导报, 2000, 18(12): 8–11.
[10] Jin XX. Translation and transmutati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China. Br J Hist Sci, 2019, 52(1): 117–141.
[11] Kimura M. The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 a review of recent evidence. Jpn J Genet, 1991, 66(4): 367–386.
[12] Darwin CR. The Origin of spec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查尔斯·达尔文. 物种起源.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3] Dawkins R. Blind Watchmaker: The Secret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Life.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6.
理查德·道金斯. 盲眼钟表匠: 生命自然选择的秘密.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14] Stiller J, Feng SH, Chowdhury AA, Rivas-González I, Duchêne DA, Fang Q, Deng Y, Kozlov A, Stamatakis A, Claramunt S, Nguyen JMT, Ho SYW, Faircloth BC, Haag J, Houde P, Cracraft J, Balaban M, Mai U, Chen GJ, Gao RS, Zhou CR, Xie YL, Huang ZJ, Cao Z, Yan Z, Ogilvie HA, Nakhleh L, Lindow B, Morel B, Fjeldså J, Hosner PA, da Fonseca RR, Petersen B, Tobias JA, Székely T, Kennedy JD, Reeve AH, Liker A, Stervander M, Antunes A, Tietze DT, Bertelsen MF, Lei FM, Rahbek C, Graves GR, Schierup MH, Warnow T, Braun EL, Gilbert MTP, Jarvis ED, Mirarab S, Zhang GJ. Complexity of avian evolution revealed by family-level genomes. Nature, 2024, 629(8013): 851–860.
[15] Steenwyk JL, Li YN, Zhou XF, Shen XX, Rokas A. Incongruence in the phylogenomics era. Nat Rev Genet, 2023, 24(12): 834–850.
[16] Aguillon SM, Dodge TO, Preising GA, Schumer M. Introgression. Curr Biol, 2022, 32(16): R865–R868.
[17] Eldredge, N & Gould, S. “Punctuated Equilibria: the tempo and mode of evolution reconsidered. ” Paleobiology, 1977, 3(2): 115–51.
[18] Abzhanov A, Protas M, Grant BR, Grant PR, Tabin CJ. Bmp4 and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of beaks in Darwin's finches. Science, 2004, 305(5689): 1462–1465.
[19] Abzhanov A, Kuo WP, Hartmann C, Grant BR, Grant PR, Tabin CJ. The calmodulin pathway and evolution of elongated beak morphology in Darwin's finches. Nature, 2006, 442(7102): 563–567.
[20] Carroll SB. Evo-devo and an expanding evolutionary synthesis: a genetic theory of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Cell, 2008, 134(1): 25–36.
[21] Gould SJ. Ontogeny and phyloge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2] Wagner A. Neutralism and selectionism: a network-based reconciliation. Nat Rev Genet, 2008, 9(12): 965–974.
[23] Mayr, E. Animal species and 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4] Carroll SB.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The New Science of Evo Devo and the Making of the Animal Kingdom.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25] Mayr E. The e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novelties. Evolution after Darwin, 1960, 1: 349–380.
[26] Simpson GG. The major features of 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27] Erwin DH. Prospects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ary novelty. J Comput Biol, 2019, 26(7): 735–744.
[28] Mayr E. What Evolution Is. Basic Books, 2001.
[29] Gehring WJ. The evolution of vision. Wiley Interdiscip Rev Dev Biol, 2014, 3(1): 1–40.
[30] Davidson EH, Erwin DH. Gene regulatory network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body plans. Science, 2006, 311(5762): 796–800.
[31] Steinmetz PRH, Aman A, Kraus JEM, Technau U. Gut-like ectodermal tissue in a sea anemone challenges germ layer homology. Nat Ecol Evol, 2017, 1(10): 1535–1542.
[32] Arendt D, Tosches MA, Marlow H. From nerve net to nerve ring, nerve cord and brain--evolu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Nat Rev Neurosci, 2016, 17(1): 61–72.
[33] Shubin N, Tabin C, Carroll S. Deep hom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evolutionary novelty. Nature , 2009, 457(7231): 818–823.
[34] Riedl R. A systems-analytical approach to macro- evolutionary phenomena. Q Rev Biol, 1977, 52(4): 351–370.
[35] Riedl R. Order in living organisms: a systems analysis of evolution. John Wiley & Sons, 1978.
[36] Müller GB, Wagner GP. Novelty in Evolution: Restructuring the Concept. Annu Rev Ecol Syst, 1991, 22: 229–256.
[37] Müller GB, Newman SA. Editorial: evolutionary innovation and morphological novelty. J Exp Zool B Mol Dev Evol, 2005, 304(6): 485–486.
[38] Gould SJ. Common pathways of illumination. Nat Hist, 1994, 103(12): 10–20.
[39] Pigliucci M, Müller GB. Evolution, the Extended Synthesis. The MIT Press, 2010.
[40] Wagner, G. , Pavlicev, M. & Cheverud, J. The road to modularity. Nat Rev Genet 8, 921–931 (2007).
[41] Gould SJ, Lewontin RC.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 Proc R Soc Lond B Biol Sci, 1979, 205(1161): 581–598.
[42] Müller GB. Evo-devo: extending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Nat Rev Genet, 2007, 8(12): 943–949.
[43] Pigliucci M. Do we need an 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Evolution, 2007, 61(12): 2743–2749.
[44] Kirillova A, Genikhovich G, Pukhlyakova E, Demilly A, Kraus Y, Technau U. Germ-layer commitment and axis formation in sea anemone embryonic cell aggregat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8, 115(8): 1813–1818.
[45] Kraus Y, Fritzenwanker JH, Genikhovich G, Technau U. The blastoporal organiser of a sea anemone. Curr Biol, 2007, 17(20): R874–R876.
[46] Technau U, Scholz CB.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ndoderm and mesoderm. Int J Dev Biol, 2003, 47(7/8): 531–539.
[47] Wagner GP. Homology, Genes, and Evolutionary Innov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48] Young NM, Hallgrímsson B. Serial hom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limb covariation structure. Evolution, 2005, 59(12): 2691–2704.
[49] Chen PJ, Dong ZM, Zhen SN. An exceptionally well-preserved theropod dinosaur from the Yixian Formation of China. Nature, 1998, 391: 147–152.
[50] Benton MJ, Dhouailly D, Jiang BY, McNamara M. The Early Origin of Feathers. Trends Ecol Evol, 2019, 34(9): 856–869.
[51] Chang WL, Wu H, Chiu YK, Wang S, Jiang TX, Luo ZL, Lin YC, Li A, Hsu JT, Huang HL, Gu HJ, Lin TY, Yang SM, Lee TT, Lai YC, Lei MX, Shie MY, Yao CT, Chen YW, Tsai JC, Shieh SJ, Hwu YK, Cheng HC, Tang PC, Hung SC, Chen CF, Habib M, Widelitz RB, Wu P, Juan WT, Chuong CM. The making of a flight geather: bio-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and adaptation. Cell, 2019, 179(6): 1409–1423. e17.
[52] Xu X, Guo Y. The 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 feathers: insights from recent paleontological and neontological data. Vertebr Palasiat, 2009, 47(4): 311–329.
[53] Saunders JW, Cairns JM, Gasseling MT. The role of the apical ridge of ectoderm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nd inductive specificity of limb parts in the chick. J Morphol, 1957, 101(1): 57–87.
[54] Meyer A, Schloissnig S, Franchini P, Du K, Woltering JM, Irisarri I, Wong WY, Nowoshilow S, Kneitz S, Kawaguchi A, Fabrizius A, Xiong PW, Dechaud C, Spaink HP, Volff JN, Simakov O, Burmester T, Tanaka EM, Schartl M. Giant lungfish genome elucidates the conquest of land by vertebrates. Nature, 2021, 590(7845): 284–289.
[55] Wang K, Wang J, Zhu CL, Yang LD, Ren YD, Ruan J, Fan GY, Hu J, Xu WJ, Bi XP, Zhu YA, Song Y, Chen HT, Ma TT, Zhao RP, Jiang HF, Zhang B, Feng CG, Yuan Y, Gan XN, Li YX, Zeng HH, Liu Q, Zhang YL, Shao F, Hao SJ, Zhang H, Xu X, Liu X, Wang DP, Zhu M, Zhang GJ, Zhao WM, Qiu Q, He SP, Wang W. African lungfish genome sheds light on the vertebrate water-to-land transition. Cell, 2021, 184(5): 1362–1376. e18.
[56] Bi XP, Wang K, Yang LD, Pan HL, Jiang HF, Wei QW, Fang MQ, Yu H, Zhu CL, Cai YR, He YM, Gan XN, Zeng HH, Yu DQ, Zhu YA, Jiang HF, Qiu Q, Yang HM, Zhang YE, Wang W, Zhu M, He SP, Zhang GJ. Tracing the genetic footprints of vertebrate landing in non-teleost ray-finned fishes. Cell, 2021, 184(5): 1377–1391. e14.
[57] Cieri RL, Churchill SE, Franciscus RG, Tan JZ, Hare B. Craniofacial feminization, social tole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behavioral modernity. Curr Anthropol, 2014, 55(4): 419–443.
[58] Holton NE, Bonner LL, Scott JE, Marshall SD, Franciscus RG, Southard TE. The ontogeny of the chin: an analysis of allometric and biomechanical scaling. J Anat, 2015, 226(6): 549–559.
[59] DeSilva J. First Steps: How Upright Walking Made Us Human. Harper Collins, 2021.
[60] Flatt T, Schmidt PS. Integrating evolutionary and molecular genetics of aging. Biochim Biophys Acta, 2009, 1790(10): 951–962.
[61] Wagner GP, Kshitiz, Dighe A, Levchenko A. The Coevolution of Placentation and Cancer. Annu Rev Anim Biosci, 2022, 10: 259–279.
[62] Kshitiz, Afzal J, Maziarz JD, Hamidzadeh A, Liang C, Erkenbrack EM, Kim HN, Haeger JD, Pfarrer C, Hoang T, Ott T, Spencer T, Pavličev M, Antczak DF, Levchenko A, Wagner GP. Evolution of placental invasion and cancer metastasis are causally linked. Nat Ecol Evol, 2019, 3(12): 1743–1753.
[63] Gould SJ. The grandeur of life: Gould's theory of the great history of biology. Taiwan: 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99.
史蒂芬·古尔德. 生命的壮阔: 古尔德论生物大历史. 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64] Sterelny K. Dawkins vs Goul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UK: Icon, 2007.
[65] Gould SJ. Is a new and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emerging? Paleobiology, 1980, 6(1): 119–130.
[66] Gould SJ. Darwin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evolutionary theory. Science, 1982, 216(4544): 380–387.
[67] Gould SJ. A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 in cerion, with comments on the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straint in evolution. Evolution, 1989, 43(3): 516–539.
[68] Martín-Durán JM, Vellutini BC. Old Questions and Young Approaches to Animal Evolution. Springer, Cham, 2019.